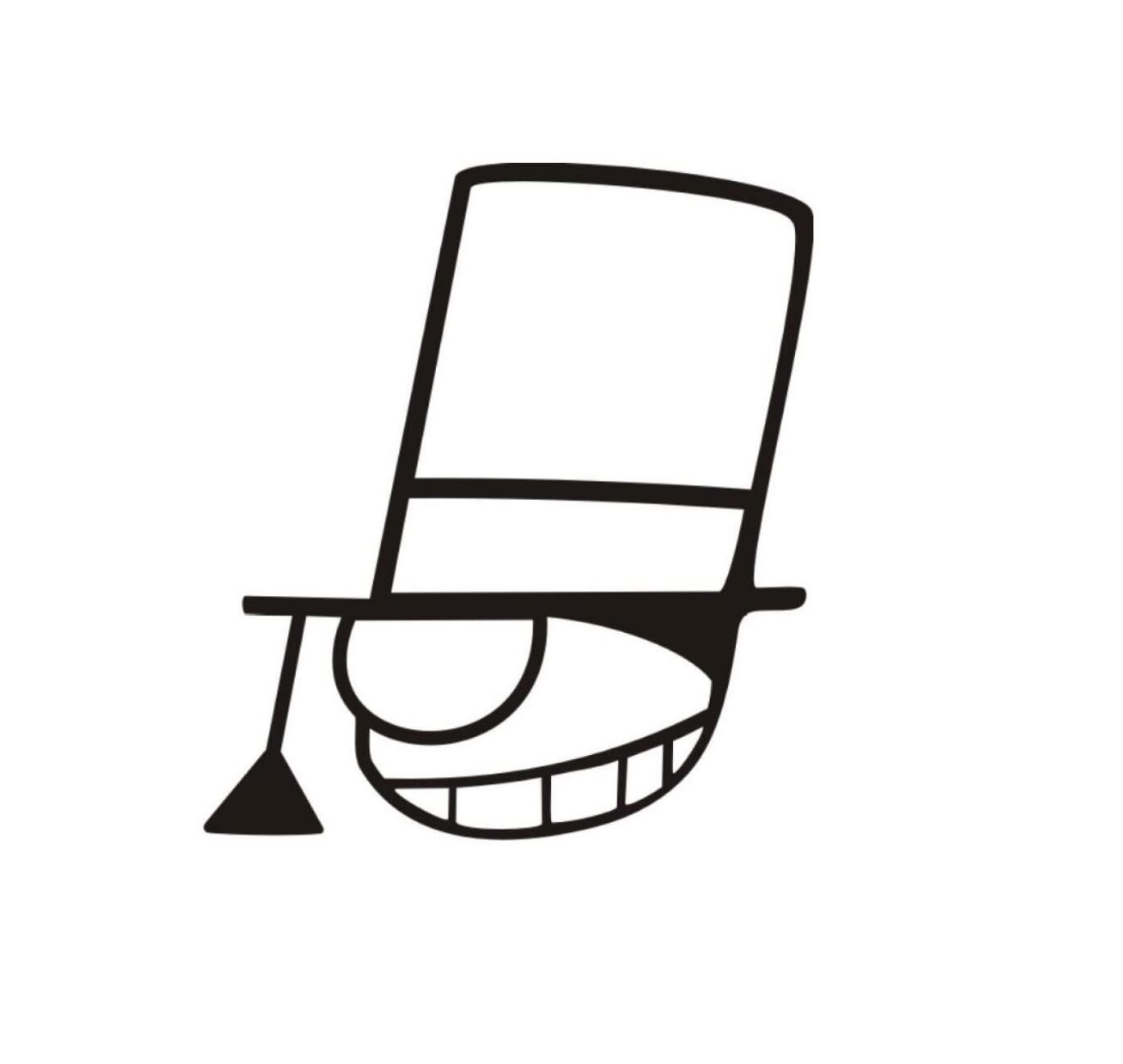第二章 手记 1
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
对我来说,所谓人的生活是难以捉摸的。因为我出生在东北的乡下,所以初次见到火车,还是长大了以后的事情。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 ,完全没有察觉到天桥的架设乃是便于人们跨越铁轨,相反认为,其复杂的结构,仅仅是为了把车站建成外国的游乐场那样又过瘾又时髦的设施。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这么想。沿着天桥上上下下,这在我看来,毋宁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俏皮游戏,甚至我认为,它是铁路的种种服务中最善解人意的一种。尔后,当我发现它不过是为了方便乘客跨越铁轨而架设的及其实用的阶梯时,不由得大为扫兴。
另外,在孩提时代,我从小人书上看到地铁时,也以为它的设计并非出自于实用性需要,而是缘于另一个更好玩的目的:即比起乘坐地面上的车辆 ,倒是乘坐地下的车辆更显得别出心裁,趣味横生。
从幼年时代起,我就体弱多病,常常卧床不起。我总是一边躺着,一边思忖到:这些床单、枕套、被套、全都是无聊的装饰品。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才恍然大悟,原来它们都不过是一些实用品罢了。于是,我对人类的节俭不禁感到黯然神伤。
还有,我也不知道饥肠辘辘是何等滋味。这倒并不是故意炫耀自己生长在不愁吃不愁穿的富贵人家。我绝不是在那样一种愚蠢而浅薄的意义上这么说的,只是我真的对 “饥肠辘辘”的感觉一无所知而已。或许我这样说有点蹊跷,但是即使我两腹空空,也真的不会有所察觉。在上小学和中学时,一旦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问道: “哎呀,肚子也该饿了吧,我们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呐。放学回家那种饥饿感,可真要人命啦 。
吃点甜纳豆怎么样?家里还有蛋糕和面包哟。”而我只顾着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那种讨好人的秉性,一边嗫嚅着 “我饿了我饿了”一边把十粒甜纳豆一股脑儿塞进嘴巴里。正因为如此,我对所谓的 “饥饿感”是何等滋味,一点也不了解。
当然,我也吃很多东西,但我不曾记得,有哪一次是因为饥饿才吃的。我吃那些看起来珍奇的东西,看起来奢华的东西。还有去别人家时,对于主人端上来的食物,我即使勉为其难也要咽下肚去。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最痛苦难捱的莫过于自己家吃饭的时候。
在我乡下的家中,就餐时,全家人一共有十个左右,大家各自排成两列入座。作为最小的孩子,我当然是坐在最靠边的席位上。用餐的房间有些昏暗,吃午饭时只见十几个人全都一声不响的嚼着饭粒,那情形总让我不寒而栗。再加上这是一个古板的旧式家族,所以,每顿端上饭桌的菜肴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不可能奢望出现什么稀奇的山珍,抑或奢华的海味,以至我对用餐时刻充满了恐惧。我坐在那幽暗房间的末席上,因寒冷而浑身颤抖。我把饭菜一点一点勉强塞进口中,不住地忖度着: “人为什么要一日三餐呢?大家都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吃饭,这似乎成了一种仪式。一家老小,一日三餐,在规定的时间内聚集到一间阴暗的屋子里,井然有序地并排坐着,不管你有没有食欲,都得一声不吭地咀嚼着,还一边佝着身躯埋下头来,就像是对着那蛰居于家中的神灵们祈祷一样。”“不吃饭就会饿死”,这句话在我的耳朵听来,无异于一种讨厌的恐吓。任这种迷信(即使到今天,我依旧觉得这是一种迷信)却总是带给我不安与恐惧。 “人因为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才不得不干活,才不得不吃饭”——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句话更晦涩难懂,更带有威吓性的言辞了。
总之,也就意味着,我对人类的营生仍然是迷惑不解。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风马牛不相及,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发狂。我究竟是不是幸福呢?说实话尽管我打幼小起,就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幸福的人,可是我自己却总是陷入一种置身于地狱的心境中,反倒认为那些说我幸福的人比我快乐得多,我和他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甚至认为,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即使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交给别人来承受,也将会置他于死地。
反正我是弄不明白的。别人苦恼的性质和程度,都是我捉摸不透的谜。实用性的苦恼,仅仅依靠吃饭就一笔勾销的苦恼,或许这才是最为强烈的痛苦,是惨烈得足以使我所列举的十大灾难显得无足轻重的阿鼻地狱。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们却能够不思自杀,免于疯狂,纵谈政治 ,竟不绝望,不屈不挠,继续与生活搏斗。他们不是并不痛苦吗?他们使自己成为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并虔信那一切理所当然,曾几何时怀疑过自己呢?这样一来,不是很轻松惬意吗?然而,所谓的人并不全部如此,并引以满足吗?我确实弄不明白 ......或许夜里酣然入睡,早晨就会神清气爽吧?他们在夜里都梦见了什么呢?他们一边款款而行,一边思考着什么呢?是金钱吗?绝不可能仅仅如此吧?尽管我曾听说过 “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但却从不曾听说过 “人是为了金钱而活着的”。不,或许 ......不,就连这一点我也没法开窍。 ......越想越困惑,最终的下场就是被 “唯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不安和恐惧牢牢攫住。我与别人无从交谈,该说什么,该怎么说,我都不知道。
在此,我想到了一个招数,那就是扮演滑稽的角色来逗笑。
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尽管我对人类满腹恐惧,但却怎么也没法对人类死心。并且,我依靠逗笑这一根细线保持住了于人类的一丝联系。表面上我不断地强装出笑脸,可内心里却是对人类拼死拼活的服务,汗流浃背的服务。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对家里人每天思考些什么,又是如何艰难地求生,不得而知。我只是对其中的隔膜心怀恐惧,不堪忍受,以致于不得不采取了扮演滑稽角色来逗笑的方式。即是说,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说真话来讨好卖乖的孩子。
只要看一看当时我与家人们一起拍的留影,就会发现:其他人都是一本正经的脸色,惟独我一个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歪着脑袋发笑。事实上,这也是我幼稚而可悲的一种逗笑方式。
而且,无论家里人对我说什么,我都从不还嘴顶撞。他们寥寥数语的责备 ,在我看来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使我近乎疯狂, 哪里还谈得上以理相争呢?我甚至认为,那些责备之辞乃是万世不变的人间 “真谛”,只是自己没有力量去实践那种 “真谛”罢了,所以才无法与人们共同相处。正因为如此,我自己既不能抗争也不能辩解。一旦别人说我坏话,我就觉得是自己误解了别人的意思一样,只能默默地承受那种攻击,可内向却感到一种近乎狂乱的狂惧。
不管是谁,如果遭到别人的谴责或是怒斥,都是不会感到愉快的。但我却从人们动怒的面孔中发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常他们总是隐藏起这种动物本性,可一旦遇到某个时机,他们就会像那些温文尔雅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蓦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般,暴露出人的这种本性。见此情景,我总是不由得毛骨悚然。可一旦想到,这种本性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格之一,便只能对自身感到由衷的绝望了。
我一直对人类畏葸不已,并因这种畏葸而战栗,对作为人类一员的自我的言行也没有自信,因此只好将独自一人的懊恼深藏在胸中的小盒子里,将精神上的忧郁和过敏密闭起来,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外表,使自己一步一步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滑稽逗笑的畸形人。
无论如何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于他们所说的那种“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总而言之,不能有碍他们的视线。我是 “无”,是 “风”,是 “空”。诸如此类的想法日积月累,有增无减,我只能用滑稽的表演来逗家人们发笑,甚至在比家人更费解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面前,也拼命地提供滑稽小丑的逗乐服务。
夏天,我居然在浴衣外面套上一件鲜红的毛衣,沿着走廊走来走去,惹得家里人捧腹大笑,甚至连不苟言笑的兄长也忍俊不禁:“喂,阿叶,那种穿着不合时宜哟!”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怜。是啊,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是那种不知冷暖,以致于会在大热天里裹着毛衣四处窜动的怪人呐。其实,我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了两只手臂上,让它们从浴衣的袖口中露出一截,以便在旁人的眼里看来,我身上像是穿了一件毛衣似的。
我的父亲在东京有不少公务,所以,他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一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回到家里时,总是给家中的人 ,甚至包括亲戚老表们,都带回很多的礼物。这俨然是父亲的一大嗜好。某一次,在上京前夕,父亲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里,笑着一一问每个小孩,下次他回来时,带什么礼物才好,并且把孩子们的答复一一写在了记事本上。父亲对孩子们如此亲热,还是很罕有的事情。
“叶藏呢?”被父亲一问,我顿时语塞了。
一旦别人问起自己想要什么,那一刹那反倒什么都不想要了。怎么样都行 ,反正不可能有什么让我快乐的东西 ——这种想法陡然掠过我的脑海。同时 ,只要是别人赠与我的东西,无论它多么不合我的口味,也是不能拒绝的。
对讨厌的事不能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事呢,也是一样,如同战战兢兢地行窃一般,我只是咀嚼到一种苦涩的滋味,因难以明状的恐惧感而痛苦挣扎 。
总之,我甚至缺乏力量在喜欢与厌恶其间择取其一。在我看来,多年以后 ,正是这种性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造成了我自己所谓的那种 “充满耻辱的生涯”。
见我一声不吭,扭扭捏捏的,父亲的脸上泛起了不快的神色,说道:“还是要书吗? ......浅草的商店街里,有一种狮子卖,就是正月里跳的狮子舞的那一种呐。论大小嘛,正适合小孩子披在身上玩。你不想要妈?”一旦别人问起我 “你不想要吗”,我已是黔驴技穷了,再也不可能做出逗人发笑或是别的什么回答了。逗笑的滑稽演员至此已是徒有虚名了。
“还是书好吧。”长兄一副认真的表情说道。
“是吗?”父亲一脸扫兴的神色,甚至没有记下来就 “啪”的一声关上了记事本。
这是多么惨痛的失败啊!我居然惹恼了父亲。父亲的报复必定是很可怕的 。
眼下如果不想想办法,不是就不可挽回了吗?那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一边打着冷颤,一边思忖着,然后蹑手蹑脚地站起身走向客厅。我来到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桌子旁边,打开抽屉取出记事本,啪啦啪啦地翻开,找到记录着礼物的那一页,用铅笔写下 “狮子舞”后才折回去睡了。对于那狮子舞中的狮子,我提不起一星半点的欲望,毋宁说倒是书还强一点。但我察觉到,父亲有意送给我那种狮子,为了迎合父亲的意志,重讨父亲的欢心 ,我才胆敢深夜冒险,悄悄溜进了客厅。
果然,我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手段取得了预料之中的巨大成功。不久,父亲从东京归来了。我在小孩的房间里听到父亲大声地对母亲说道:“在商店的玩具铺里,我打开记事本一看,嗨,上面竟然写着 "狮子舞 "。那可不是我的字迹呢。那又是谁写的呢?我想来想去,总算是猜了出来。原来是叶藏那个孩子的恶作剧哩。这小子呀,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嗤嗤笑着,默不做声,可事后却想要那狮子想得不得了。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呐。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自个儿却一板一眼地写了上去。
如果真是那么想要的话,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所以呀,我在玩具铺里忍不住笑了。快把叶藏给我叫来吧。”我把男女佣人召集到房间里,让其中的一个男佣胡乱地敲打着钢琴的琴键(尽管这是偏僻的乡下,可在这个家里却几乎配备了所有的家什) 。我则伴随着那乱七八糟的曲调,跳起了印第安舞蹈供他们观赏,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哥则点上镁光灯,拍摄下了我的印第安舞蹈。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 ,从我围腰布的合缝处(那围腰布不过是一块印花布的包袱皮罢了) ,竟露出一个小雀雀。顿时这又引来了满堂的哄笑。或许这也可以称之为以外的成功吧。
每个月我都定购不下十种新出版的少年杂志,此外,还从东京邮购了各种书籍,默默地阅读。所以,对麦恰拉克恰拉博士呀,纳蒙贾博士呀,我都颇为熟悉。并且对鬼怪故事、评书相声、江户笑话之类的东西,也相当精通。因此,我能够常常一本正经地说一些滑稽的笑话,令家人捧腹大笑。
然而,呜呼,学校!在学校里我也开始受到了众人的尊敬。 “受人尊敬”,这种念头本身也让我畏葸不已。我对受人尊敬这一状态进行了如下定义:近于完美无缺地蒙骗别人,尔后又被某个全智全能之人识破真相,最终原形毕露,被迫当众出丑,以致于比死亡更难堪更困窘。即使依靠欺骗赢得了别人的尊敬,无疑也有某个人熟谙其中的真相。不久,那个人必定会告知其他的人。当人们发觉自己上当受骗后,那种愤怒和报复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即使稍加想象,也不由得毛发竖立。
我在学校里受到众人的拥戴,与其说是因为出生于富贵人家,不如说是得益于那种俗话所说的 “聪明”。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常休学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曾经卧床休息过一学年。尽管如此,我还是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搭乘人力车到学校,接受了学年末的考试,殊不知比班上所有的人都考得出色。即使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也毫不用功,纵然去上学,也只是在上课的时间里一直画漫画,等到下课休息时,再把它们展示给班上的同学看,说明给他们听,惹得他们哄堂大笑。而上作文课时,我尽写一些滑稽故事 ,即使受到老师的提醒,也照写不误。因为我知道,其实老师正悄悄地以阅读我的滑稽故事为乐呢。有一天,我按照惯例,用特别凄凉的笔调描写了自己某一次丢人现眼的经历。那是我跟随母亲去东京的途中,我把火车车厢里通道上的痰盂当成了尿壶,把尿撒在了里面(事实上,在去东京时,我并不是不知道那是痰盂才出的丑,而是为了炫耀小孩子的天真无知故意这么做到) 。我深信,这样的写法肯定能逗得老师发笑。所以就轻手轻脚地跟踪在走向教员休息室的老师背后。只见老师一出教室,就从班上同学的作文中挑出我的作文,一边走过走廊,一边开始读了起来。他 “嗤嗤”地偷偷笑着,不久便走进了教员休息室。或许是已经读完了吧,只见他满脸通红大声笑着,劝其他老师也立即浏览一遍。见此情形,我不由得心满意足 。
淘气鬼的恶作剧。
我成功地让别人把这视为 “仅仅是一个淘气鬼的恶作剧罢了”。我成功地从受人尊敬的恐惧中逃离了出来。成绩单上所有的学科都是十分,唯有品行这一项要么是七分,要么是六分,这也成了家里人的笑料之一。
事实上,我与那种淘气鬼的恶作剧本质上是恰恰相悖的。那时,我被男女佣人教唆着做出了可悲的丑事。事到如今我认为,对年幼者干出那种事情 ,无疑是人类所能犯下的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行径。但我还是忍受了这一切,并萌生了一种感觉,仿佛由此而发现了人类的另一种特质似的。我只能软弱地苦笑。如果我有那种诉说真相的习惯,那么,或许我就能够毫不胆怯地向父母控诉他们的罪行吧,可是,我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一点也不指望那种 “诉诸于人”的手段。无论是诉诸父亲还是母亲 ,也不管诉诸警察,或是政府,最终难道不是照样被那些深谙世故之人强词夺理击败了吗?不公平现象是必然存在的。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事实。本来诉诸于人就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依旧对真实的事情一言不发,默默忍耐着除了继续扮演滑稽逗笑角色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嘲笑道: “什么,难道不是对人类的不信任吗?嘿,你几时当上了基督教徒?”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与宗教之路直接相通。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难道人们不都是在相互怀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的吗?记得自己小时候,父亲所属的那个政党的一位名流来到我们镇上演说,男佣人带着我去剧场听讲。听众密密匝匝地挤在那里,我看见了镇上所有与父亲关系密切的人的面孔。这使我兴奋不已。演讲结束后,听众们三五成群地沿着雪夜的道路踏上了归途。信口开河地议论着演讲会的不是,其中还掺杂着一个和父亲过从甚密的人的声音。那些所谓的 “同志们”用近乎愤怒的声调大肆品头论足,说什么我父亲的开场白拙劣无比,那位名人的演讲让人云里雾里,不得要领等等。更可气的是,那帮人居然顺道拐入我家,走进了客厅,脸上一副由衷的喜悦表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甚至当母亲向男佣们问起今晚的演讲会如何时,他们也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真是太有趣了。”而正是这些男佣们刚才还在回家的途中叹息说: “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了。”而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相互欺骗,却又令人惊奇地不受到任何伤害,甚至于就好像没有察觉到彼此在欺骗似的,这种不加掩饰从而显得清冽、豁达的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人类生活中比比皆是。不过,我对相互欺骗这类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依靠扮演滑稽角色来整天欺骗人们。对于那种教科书式的正义呀、道德之类的东西,我不可能抱有太大的兴趣。在我看来,倒是那些彼此欺骗,却清冽而开朗地生存着,抑或是有信心清冽而开朗地生活下去的人,才是令人费解的。
人们最终也没有教给我其中的妙谛。或许明白了那些妙谛我就不再那么畏惧人类,也不必拼命提供逗笑服务了吧。或许也就犯不着再与人们的生活相对立从而体验那种每个夜晚的地狱所带来的痛楚了吧。总之,我没有向任何人控诉那些男女佣人犯下的可恨罪愆,并不是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 ,当然更不是基督教的影响,而是因为人们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关闭了信誉的外壳之缘故。因为就连父母也不时向我展示出他们令人费解的部分。
然而,众多的女性却依靠本能,嗅出了我无法诉诸于任何人的那种孤独气息,以致于多年以后,这成了我被女人们乘虚而入的种种诱因之一。
既是说,在女人眼里,我是一个能保守恋爱秘密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