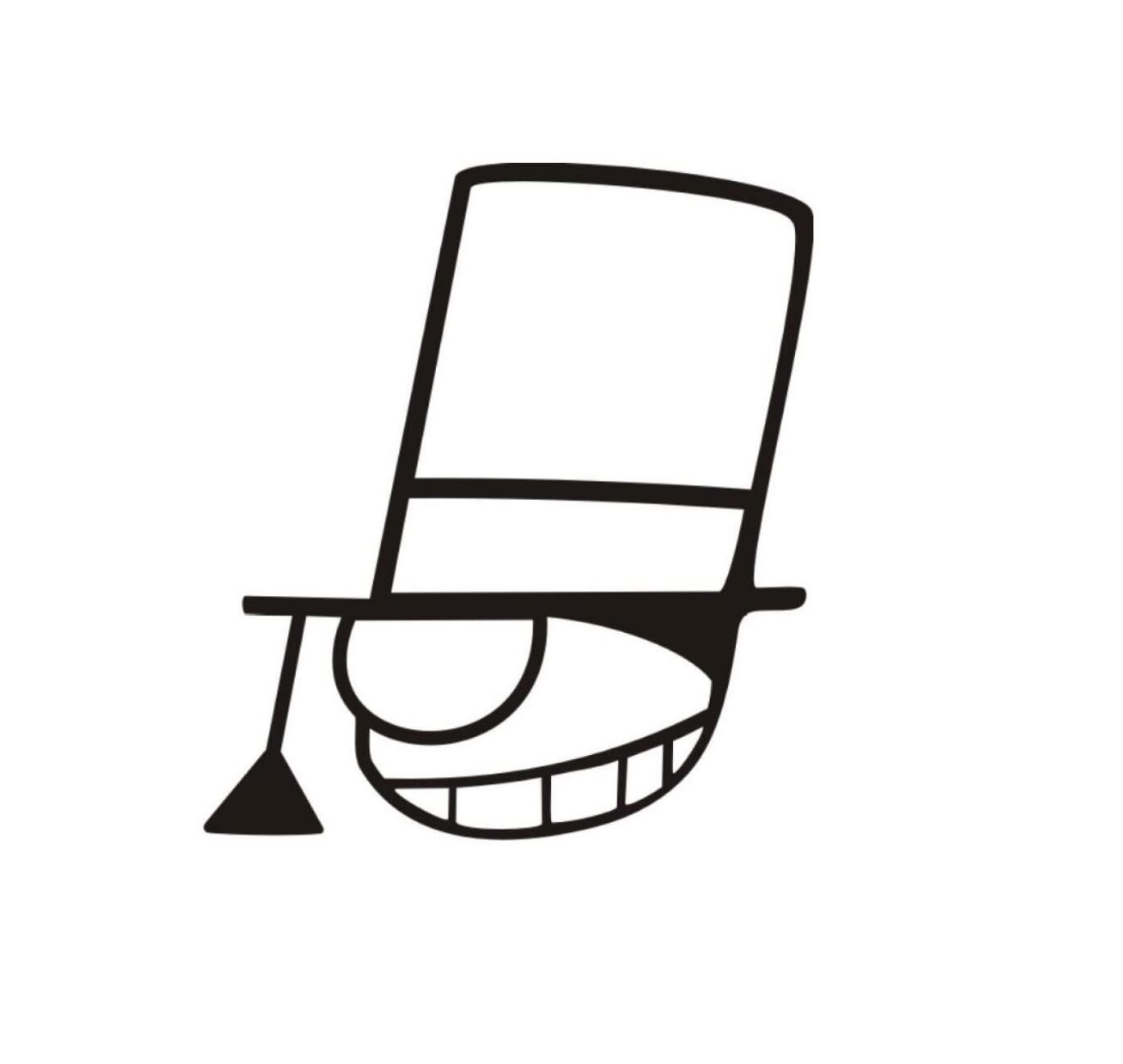第四章 梦的改装
假如我现在就声称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实现”,我确信必会招致最强烈的辩驳。批评我的人将会说:“梦能够被解释为‘愿望的实现’的说法,其实不是创举,过去如:拉德斯托克、沃尔克特、普金吉、格利辛格尔等已有此论,但要说在以“愿望的实现”为内容以外,就没有其它梦,那就未免以偏概全,成为站不住脚的谬论。反之,充满不愉快内容的梦,却是常见的。悲观哲学家哈特曼最反对这种‘梦是愿望实现’的观点。在他《潜意识的哲学》的第二部里,他说:“……至于梦,可认为是日间活动中,除了理性上、艺术上较惬意的享受之外的,一切烦恼全部带入睡境所造成的结果。
事实上,甚至别的一些不大悲观的观察者,也都同意梦里痛苦不祥的内容要比愿望实现的情形多些。有两位女士,韦德和哈拉姆曾用她们自己的梦,以统计数字表示出梦较多沮丧失望的内容,她们发现百分之五十八的梦是不尽如人意的,而仅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六方是愉快的内容。除了那些带入我们梦境中的痛苦以外,还有一些令人无法忍受,甚至把人惊醒的‘焦虑的梦’。也就是这种梦常使小孩睡觉时吓得惊醒而大哭大叫。然而最显然的愿望实现的梦,也只有在儿童中才能产生。因此梦未必全是‘愿望的实现’。”
由此看来,似乎“焦虑不安的梦”的实例,足以推翻前面所提的梦,而且还可因此指斥愿望实现的说法为无稽之谈。
但是,要想对以上这种好像是振振有词的反调给以辩驳也并不难,我们只需注意到,我们对梦的解释不是就其梦的表面内容作的解释,而是以探究梦里头所隐藏的思想内容所作的解释。现在让我们来认真比较一下梦的显意与隐意吧!梦的显意,确实常常是令人痛苦的,但有谁曾花精力去找那隐藏在其中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呢?若是没有下过这份功夫,那么所持的两种反对论调也就经不起推敲!因为我们那些痛苦的梦,假如经过潜心分析的话,又有谁敢说它不是蕴涵着愿望实现的意义呢?
在科学的研究中,当一个难题解不开时,莫如再加上一道难题,一同来考虑,有时反而能找到意外的解决办法。就像你把两个胡桃核凑在一起敲碎,比一个个分别敲碎容易。所以,我们现在不只要解决这一个问题——“痛苦的梦,如何解释为‘愿望的实现’?”还要再考虑另一个我们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何以那些粗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梦,需要通过层层辨析,方可看出也是愿望实现的意思呢?”就以伊玛打针这件事情来说,这并非一个痛苦的梦,并且经过解析,得以充分看出,确实是“愿望的实现”,但为什么必须得经过这段解释呢?难道就无法直接看出它的意义吗?实际上,伊玛打针的梦,以表象看来,无论是读者们乃至做梦者本人,在分析之前,都无法看出竟是做梦者愿望的实现。若是我们把“梦是需要解释的”看作是一种梦的特点,将其称为“梦的改装现象”,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梦的改装的来源是什么?”
至于梦这个问题,很多可能的问题都将被提出,例如有人认为,睡觉时一个人是无法对自己的梦中想法有个切实的表达的。或者说,梦的分析需找出另一种解说。因而,我将在这里再举出我自己的第二个梦,当然也难免会把个人的一些私事鲁莽地公布于众,以便能作更清楚地解释,但是我确信这样做是值得的。
前言
在一八九七年春季,我得知有两位我们大学的教授,推举我升为临时教授(profess or extraordinarius,大致相当于助教)。这消息真的令我极为高兴,而且也对两位杰出人物对我的垂青感到难以相信。我立刻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不要太期待奇迹的出现,因为过去几年,校方已经数次拒绝这种推荐,而且还有许多比我资深的或同年的同事,也都已等待了几年,却毫无消息。而我自认为并不比他们高超多少。因此,我决定还是宁肯听任自己失望,也决不乱存奢望。我自知自己并非是有野心之辈,而且虽没有那种教授身份,但我过得还算十分惬意。或许那葡萄是吊得过高了吧,也使我难免有酸葡萄之讥!
在一个晚上,一位朋友R先生来看我。他的遭遇始终是使我引为他山之石而自戒的。他很早就已被推荐为教授头衔(对病人而言,有了这头衔的人有如神仙一般的神气),而他也比我较不死心,因而经常向上司追问何日晋升的可能性。这一次他告诉我,他在忍无可忍之下,坦白地逼问上司,他之所以迟迟未能晋升的原因是否与他本身的宗教派别有牵连。结果上司的答复是,目前由于众议,他的确无法晋升,他说:“至少目前我已清楚我自己的处境。”我这朋友所告诉我的并非是什么新消息,但至少他增加了我的自知之明,因为我和他是同样的教派。
在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就把当晚所做的梦记录下来了,它包括两种想法和两个人物,而一个想法紧跟着的便是一个人物,在梦中分为两部分出现。但在这里,我只需提出这梦的上半部,因为下半部与我这里所要说的无多大关系。
一、“我的朋友R先生”是“和我极有感情的叔叔!”
二、“我很近地看着他的脸,有些变了形,似乎脸拉长了,腮边上长满黄胡子,看来很有特色”,接着有两个别的梦,一个人物和一个想法,我就此从略。
这怪梦的解释如下:
当天早上我回想这个梦时,我不觉付之一笑,“嘿!多么无聊的梦!”但是,我却始终不能释怀,并且整天出现在脑中。终于到了晚上,我开始责备自己,“当我自己在对病人作梦的解释时,假如他们说他的梦太荒唐、太无聊、不值得一提,我自己也一定会怀疑中间必有隐情,而且非探个水落石出不可。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之所以觉得不值得一提,正表示着心中有着怕被分析出来的阻力。“嘿!可千万别让自己溜过去!”所以我就开始分析工作了。
“R先生是我的叔叔”: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有一个叔叔,叫做约瑟夫。说起我这位叔叔,真是很可怜,约在三十多年前,一时为了再多赚点钱,竟去触犯刑法,被判了刑。我父亲为了这件不幸的事,在几天之间,头发就变白了。他常说约瑟夫叔叔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大呆子”。那么,假如我梦见R先生是个大呆子,这种论调也太没道理,但我的确在梦中看到那副相貌——长脸黄须,而我叔叔就是长脸,两腮上有迷人的黄胡子。但R先生却是个黑发黑须的家伙。当青春不再时,那黑发是会变灰的,而黑胡子也会一根根地由黑色而变为红棕再成为黄棕,最后变为灰色。R先生现在的须色,恰恰是连我见了也伤心的那副苍老颜色。在梦里,我似乎既见到R先生的脸,同时又见到叔叔的脸,有如高尔顿(Galton)的复合照相术——高尔顿擅长把几张长相酷似的面孔重复地感光于同一底片上。因此看来,显然是我心中认为R先生是个大呆子,就和我那叔叔一样。
到现在,我从自己这份解释中还是看不出究竟。我想这中间一定包含某种动机,使我毫不留情地想揭发R先生。但是,事实再明显不过:我叔叔本是个犯人,而R先生决不是什么犯人。喔!对了,他有一次由于骑自行车撞伤了一个学徒而被罚款。难道我会把这事放在心里了吗?这种对比简直是太荒唐了。这时,我又忆起几天前,我与另一位同事N先生的谈话。其实,谈话内容也不外乎那升迁的事。我与N先生在街上相遇,他也被提名为晋升教职,并且他也听说我最近被推荐为副教授的消息,他当场恭喜我,而我拒绝了他。我说:“你可不要再这样揶揄我了,实际上,你也明白现在只是被人提名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他略带勉强地回答:“你可不要这样说,我因为自己有问题,才升不了的。你难道不知道那女人告发我的事吗?我可以告诉你,那案子其实根本就是一种卑鄙的敲诈,而我只是尽力想使那被告免于被判刑而招来麻烦,很可能那件事深刻地印在部长的记忆中了。但你呢?可完全是清白的呀!”就这样,我又由梦的解释与趋向引出了一个罪犯人物,我的叔叔约瑟夫代表我的两位被提名晋升教职的同事——一个是“大呆子”,一个是“罪犯”。直至现在,我才明白了这梦之所以要解释的地方。假如教派的歧视确实是我那朋友得不到晋升的症结所在,那我的晋升同样是无望了。但假如我能找出这两位同事身上我所不存在的其他缺点,那我的晋升希望就不会受到影响。这就是我做梦的程序。梦将R先生变成了大呆子,N先生又变成了罪犯,而我却既不是呆子,也不是罪犯,于是我便大有希望晋升了,而且不必担忧R先生告诉我的那桩坏消息。
写到这里,总觉得意犹未尽,对于这份解释的内容,也仍旧不太满意,特别是为了自己晋升高职,竟在梦中如此歪曲那两位我素来敬仰的同事,更是自责不已。幸好,鉴于我自己深知由梦中所分析出的内容,决不是真正的事实,多少也可减轻一下对自己的责备。实际上,我绝对不能相信有人敢说R先生是个大呆子,同样地决不相信N先生会被牵涉在敲诈事件中。当然,我也不相信伊玛真的是因为奥图给她打的那丙基针而病情恶化。总之,如以前所示,梦里所表现的皆是一厢情愿的实现。就愿望实现的内容看来,我的第二个梦,好像比第一个梦来得较不离谱,但实际上,也有些蛛丝马迹勉强可以说明这些或许是事实的毁谤,从而发现这梦的确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当时我的朋友R先生正被他同系的某教授反对,而且我另一位朋友N先生,也私下里悄悄告诉过我一些有关他的不可告人的私事。但我仍要再重申一下我的看法,这个梦还须再深入地解析下去。
现在我忆起那个梦还有一些刚才释梦时未注意到的部分。当我在梦里发现R先生就是我叔叔时,我心里对他产生一种深厚的感情。但究竟这份感情实际上是对谁呢?当然,对我那个约瑟夫叔叔,我可从来没有这般深厚的感情,而R先生虽与我是长年之交的好友,但如果我当面对他叙述我梦中对他所具有的那份深厚感情,无疑地,他必定会感到肉麻。假若我这份感情是针对他的话,以我理智的分析,完全是揉合了他的才华与人格,进而又掺杂进我对叔叔所产生的那种矛盾的感情的夸大,而这份夸大竟是朝着相反方向走的。现在,我终于发现,这份难以言说的感情,并不属于梦的意境或内含的念头,而恰恰相反,它反过来是与梦的内容相违背的,而且在梦的分析过程中,巧妙地躲过了我的注意力,极可能这便是它的主要功能。我还记得,就在我做这梦的分析前,曾是多么地不情愿,我尽量推迟时间,还一味地嗤之以鼻;而今,从我多年对精神分析的经验看,我深知这种“拖延”、“嗤之以鼻”更表现出其中大有文章。实际上,这份感情对梦的内容而言,并无多少关联,但起码表达了我内心对这梦的内容所产生的实在感受。若是女儿不爱吃苹果,她常常连尝都不尝一口就说那苹果特别苦,若是我的病人采取这种行动,我也会马上可以猜到他必有所潜抑。同理,我的梦也是这样。我之所以迟迟不肯去解释这个梦,也不外乎是我对其中某些内容产生了反感,现在,经过如此抽丝剥茧地研究,我方知道我反对的是把挚友R先生变为大呆子,而我在梦中对R先生那种非同寻常的感情,其实并非是梦里真正的感情,而仅是表示我内心对这释梦工作反感的强烈程度。如果那时,我的梦在一开始就被这个感情所困惑,而获悉与现在相反的解释,那么我梦中的那份感情便会实现它的目的。也就是说,这感情是有目的的,希望能使我们对梦作改装。我在梦中对R先生恶意中伤,并且不会使我相反的一面——一种确实存在的温厚友谊——浮现到梦的意识来。
上述所发现的道理,推广到各方面都是能够成立的,就如第三章我们所提出的梦,有些是极为简单的愿望达成,而一旦愿望的达成有所“伪装”或“难以辨认”,则会表示梦者本身对此愿望存有顾忌,并且会使这愿望只能以另一种改装的形式来表达。我将在实际的社交生活中找出一些与此内心活动相类似的实例。在社交中,我们有许多虚伪客套,就两个人在一同工作来说,若是其中一个有某种特权,那么另一位必定对他这份特权时时有所顾忌,那么他只得对他自己内心想做的行为有所改装,也就是说,他就得戴上一副假面具。实际上,每天我们待人时所应用的礼节,说穿了只不过是这种虚伪。假如为了读者们,我要对我的梦作诚实的解释的活,那我势必要陷入这种自己撕破假面具的尴尬场面。甚至连诗人们也在抱怨这种虚伪的必要性:“能贯通的最高真理,你都不能坦白地告诉学生们。”(歌德《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费勒斯的两句话。)
政论作家也同样地对那些执政者有所顾忌,而把很多令人不快的事实加以掩饰。假如他敢坦率地写,那么政府无疑地必会予以制裁——口头上发表的,事后必被整肃警告,而已出版成书的,也必被禁印封闭,因而作者们为了检查者的缘故,不得不对其言论作些伪装,不是完全只字不提地明哲保身,而是旁敲侧击地将那些曾被反对的言论予以巧妙的改装。例如,他会以两个中国满清贪官污吏的劣迹,来嘲讽其国内有问题的官员,而且通常检查标准越是严格,作家们便越有更巧妙的方法来暗示读者真正的含义。
这种检查,致使作家所作的改装完全类似于我们梦里所作的改装,那么如今,我们须假设每个人在自己的心灵内都有两种心理步骤,或称之为“倾向”、“系统”。第一个是在梦中表现出愿望的内容,而第二个却扮演检查者的角色,而形成了梦的“改装”。但第二个心理步骤的权威性,究竟是否靠那些特点来做它的检查呢?假如我们想到,那些梦的隐意均经过分析方可为我们所意识到,而醒来后意识到的只是梦的显意时,我们必能得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凡能为我们所想到的,必须经过第二个心理步骤所认可;而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材料,如果不能通过第二关,则不能为意识所接纳,而只能任由第二关加以各种变形直至它满意的地步,才能够进入意识的境界。因而,我们就此获得所谓意识的基本性质: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它是感官将其他来源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而形成的产品。而对心理病态来说,我们决不可对“意识”这一重要问题有任何忽略,因此我计划以后再另作更详尽的探讨。
我用以上所述那两种心理的步骤与“意识”的关系,来证明我对R先生虽具有深厚感情,而在梦中却加以如此轻蔑态度的现象,我发现在政界官场里,我也同样能找出一些类似的现象。就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他扩张私人权力的欲望通常与人民意见是相违背的,因而他往往就会采取一种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做法:他会故意将那些人民极厌恶的官员加以器重,给予他们某些本不应该得到的特权,因而或多或少发泄出他对人民意见的藐视。同样,我这控制意识的第二个心理步骤,也由于第一个心理步骤的希望——对R先生具有极深的感情,而将那隐藏着的冲动以“把他贬斥为一个大呆子”来发泄掉。
或许我们会怀疑,经过梦的分析,我们能否得以解开哲学所一直无法解决的人类心理问题,但是,目前我并不准备以此途径去发展,我们还应先返回去把“梦的改装”先阐释清楚,主要问题是梦中不愉快的内容到底如何解释为愿望的实现。我们现已看出,所表现的不愉快内容不外乎是愿望实现的一种变相的改装。用一句我们前面提到的假设,我们也能够说,梦之所以要改装成不愉快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由于其中某些内容为第二心理步骤所不准许,而同时这部分恰是第一心理步骤所需要的愿望。每个出自第一心理步骤的梦,均为愿望的实现,第二心理步骤却横加破坏裁减,而毫无增润。假如我们只考虑到第二心理步骤对梦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对梦将永远不能作出准确的认识,而本书作者发现的这些梦的问题,也将得不到解决。
欲证明每一个梦的秘密意义确实在于愿望的实现,的确需要一番分析工作,因此,我将特意选些痛苦的梦,尝试对它作一番分析,其中有些是“歇斯底里症”患者所做的梦,因而须附带一些长篇的“前言”,并且有些部分也会涉及到患者心理过程的分析——这些,不可避免地将会是令读者倍感困惑的。
当我治疗心理症的病人时,他的梦常常就成了我们讨论的关键。我必须随时靠他本身的帮助来对梦中的各种细节加以分析解释,从而知道他的病情,此时我就常会受到比我的同事对我的批评更厉害的反驳。差不多所有病人都不赞成我的“梦是愿望的实现”这种说法。以下就是一些被引出来驳斥我观点的梦的内容。
“你总是说,梦是愿望的实现。”一位相当聪明的女病人告诉我,“但我立刻就可以说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梦。梦中我的愿望完全无法实现,这下看你怎样自圆其说。梦是这样的:我梦见我想准备晚餐,但手头上就只有熏鲑。我想出去买东西,偏巧是礼拜天下午,所有商店都关门休息。那就打个电话给餐馆,偏偏电话又断了线。最后我只好死了这份做晚餐的心。”
我回答她,诚然,你这梦乍看起来似乎非常合理地完全与我的理论相悖——完全是不能实现的愿望,但是,梦的真正意义总是要经过分析的,决不是仅用表面意义所能代表的,于是我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你做这些梦的呢?你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解析
这病人的丈夫,是一个忠厚而且能干的肉贩子,在一天前告诉过她,他自己实在是胖得太快了,有必要去接受减肥治疗。今后他会早起、运动、节食,而且更重要地,他再也不接受任何晚宴的邀请。她就取笑他,说有一次她丈夫在他们常去的饭馆里结识了一位画家。那画家执意要为他画张像,并且说,他一生中还从未见过像他这般生动的面孔,但被她丈夫坦率地拒绝了。她丈夫认为,任何一位漂亮女孩的屁股都会比他的面相更能打动画家。(歌德的诗句“如果没有屁股,这位贵人如何坐着?”也许给了他灵感。)她深爱着她丈夫,也因而痛快地取笑了他一番,并且央求他以后不要再给她“鱼子酱”。这句话又有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她一直希望每天早餐都能有三明治加鱼子酱,但是出于俭朴的习惯,使她不能这样做。同时她深知,如果她开口要求,她丈夫一定会立即买给她吃的,但是与此相反,她却要求他不要给她鱼子酱,以便以后她还能够再以这事来揶揄他。
就我看来,这段解释仍非常勉强。不满意的解释常常是背后仍隐藏着一段未坦陈的告白。我想起米伯恩海姆做过催眠的那些病人。当他对病人做“催眠后的指示”时,他问到他们的动机时,他们的回答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并不知道我何以这样做”,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都会编造出一个看得出破绽的理由来。这与我所提的那位女病人的鱼子酱故事是有点相似的。我们能够明白她是在清醒状态下,下意识地编造了一个所不能实现的愿望,她的梦也同样地显示了愿望的不能实现。但她何以需要不能实现的愿望呢?
到现在所得到的资料,仍不足以对梦作一番真正的解释,于是我就逼问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才终于克服了阻力。她想到,一天前她曾去拜访一位她先生经常称赞的令她多少有些妒意的女友。还好,她丈夫最喜欢身段丰满的女人,而她发现那女友长得瘦长多了。再追问下去,她又说了,那女友曾告诉她,她恨不能长胖些,并且问她:“你何时能邀我吃饭呢?你的菜永远都做得那么好!”
到此,我们总算能够对这梦作一番合理的解释了!我终于能告诉病人:“其实在你那女友希望你请客时,你心里就有数:‘哼!我才不请你去我家呢,如果真使你长胖了,再让我先生动非分之想,那我宁愿晚餐都不煮呢!’而你现在所做的梦,正是说你做不成晚餐,因而实现了使你那女友长不丰满的目的。你丈夫所提出的减肥妙方最重要的就是不参加人家的晚宴,于是在你的心里,你就产生了这个念头:‘到人家家里吃饭才能长胖。’现在,似乎所有的疑团都解释清楚了吧!且慢!还有‘熏鲑’这东西。也具有什么意义吧?你在梦中,何以会想到熏鲑这道菜呢?”“熏鲑是我那女友最喜欢的一道菜。”恰巧,我也认识她这位女友,而我深知这妇人节俭到舍不得吃熏鲑的程度,与我这病人爱吃又不忍花钱吃鱼子酱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梦,再加上附带的细节,使我感到有必要再作另一种解释。这两种解释方法决不相互冲突,反而更能由此看到梦境的全貌,并且也可由此看出一般心理病态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暧昧性。我们已经知道这女病人曾梦到对自己愿望的否定(想吃鱼子酱的愿望〕,而她的那位曾表示过盼望长胖的女朋友,如果在我们这位病人的梦中永远长不胖的话,那我想我们肯定一点也不惊讶,但是,事实上她只是梦到她本人吃鱼子酱的梦无法实现,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梦作一新的解释:梦中她不能如愿,其实不是指她本人,而是在梦中以自己代替了那位朋友的位置。用句心理学的术语,就是说她把自己“仿同”成她那朋友那样。
我想,她确实是如此地仿照了那女友,而变成了自己的不能如愿。但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仿同作用”有何意义呢?要说明这问题就需要再进一步地探讨了。“仿同作用”是导致歇斯底里症状极为重要的动机。病人通过这种作用,不仅能将自己本身的经验以某种症状表现出来,也能够以通过别人的许许多多其他经验,表现出各种千奇百怪的、不能解释的症状。
他们有时就像真能扮演人生百态的角色。或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所谓的“歇斯底里的模仿”——歇斯底里的病人确有能力模仿一些发生在别人身上,但却令他们印象非常深刻的症状,而且借以这种模仿能够得到所需的同情。但是,这仅仅是说明了歇斯底里模仿的心理过程与所循的途径罢了。而途径本身与循此途径所需的“精神行动”却完全是两码事。“行动”本身比我们所想象的歇斯底里模仿实在要复杂得多,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潜意识的最后产品。举个实例来说:医生与一群精神病人同住一段时间后,有一天,他或许就会发觉某个病人突然发作类似另一女病人所发作过的肌肉抽搐。这时,这位医生也许会司空见惯地说:“那是由于这病人曾看过这女病人的发作状态,从而模仿了她。”这就是所说的“心理感染”。但是,心理感染有时却是用以下这种方式发生的:一般情况下,病人们彼此间的了解较医生对他们个别的了解反而会更多,一旦医生查访了某位病人之后,他们便会对他反复询问,给予更大的关切。若是今天有一位病人发作了,立刻他们就会知道那是因为刚接到的一封信触发了他的相思病或别的心病,于是很快引起了他们的同情心。而且虽然未进入他们自己的意识界,但他们心中却会形成这样一个结论:“假如这种原因会引起这种症状,那么有这种问题的我,可能也会发生这种症状吧!”假如这个结论进入了意识界,那么他就会成天担心这种症状的降临;但如果它只是深藏于潜意识里,那么就会于不知不觉中产生他们真正所害怕的症状。因此,“仿同作用”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基于同病相怜的同化作用,再加之某些滞留于潜意识的同样状况发作时所造成的结果。
在歇斯底里症里,“仿同作用”尤其常用于与性相关联的方面,这种病的女患者通常将自己仿同成与她本人有过性关系的男人,要不就是扮成那些曾与她的丈夫或情夫有过暧昧关系的女人。我们在爱情中所讲的话——“永结同心”、“形影不离”也正说明了这种仿同的倾向。在歇斯底里的幻想或梦境中,通常一个人只要想到性关系,而不一定实际发生,就能够很容易地产生仿同作用。我们所举的这女病人,她只是循着其歇斯底里的思路。她对她女友的嫉妒(对这解释,她是始终拒绝承认的)导致自己在梦中代替了她女友的身份,而仿同她来编造出一个症状(愿望的否定)。进一步解释如下:在梦里,她代替了那位朋友,是因为她的女友获得了她丈大的欢心,而她自己内心极盼望能夺回她丈夫对她的珍重。
还有我的另一位女病人,一位极其聪明伶俐的妇人,也做了一个与我的理论完全冲突的梦,但我也还是按着我那“一个愿望的未能实现,其实象征着另一愿望实现”的原则,很顺利地解决了她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告诉这病人,梦是希望的实现。而第二天,她就对我说,她梦见她与她婆婆一起去避暑。但我早已知道,她极不愿意与她婆婆住在一起度过这夏天。并且,我也听说她十分高兴,因为已经在距离她婆婆要去避暑的地方很远处租到了房子。因此,这个梦看来似乎又与我的理论背道而驰。
难道这就能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吗?由这梦的推论所得的解释来看,我是完全错了。但实际上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的理论都是错的,而这梦也就恰恰满足了她这种希望,她之所以希望我有错误,事实上是一件严重的问题。因为,她在接受我心理分析治疗期间,在由她所提供的资料中,我曾分析出她生命的某个阶段内,曾有某些事情的发生与她现在的病情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她却以完全记不起来而否认。但过了不久,经过一番追问,她不得不承认我的断言确实是正确的,也因为此,她心中就不自觉地希望有一天能证明我的话是错误的,于是她就将此愿望变为,梦中与她婆婆一同下乡避暑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荒诞怪事。
现在,我再任意举几个小例子,不用分析,单凭一些假设、也可看出一些释梦的端倪。有一位与我同窗八年的律师朋友,有一次在小聚时,听我给他们介绍了关于梦是愿望实现的理论。回家后,他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的一切讼案全部败诉。于是他就对我抱怨了一番。当时,我只得推说:“风水轮流转。一个人毕竟无法永远胜诉吧!”但我在私下却想:“八年同学期间,我一直名列前茅,而这家伙成绩却始终平平,因此他内心会不会总有个想法,希望有一天我也会表现得只不过尔尔呢?”
还有一个女病人,讲了一个更悲惨的梦来驳斥我的理论。这病人是位年轻的女孩,以下便是她的独白:“你总还记得我姐姐现在仅有一个儿子查理吧,她那长子奥图在我尚与他们同住在一起时便夭折了。我那时最疼爱奥图,而且他差不多完全是由我带大的。当然,我也很喜欢查理,可是他总不如奥图那么惹人爱。昨晚,我竟然做了一个怪梦,我梦见查理僵硬地躺在小棺木里。两手交叉平放,周围插满了蜡烛。总之,那样子很像当年奥图死时的情景。现在,请你回答我,到底这梦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了解我的,难道我真的那般狠心地期望我姐姐连那仅剩的一个宝贝儿子都死去吗?或者说,这梦只是表示出我宁可查理去替我那宝贝的奥图去死呢?”
我向她保证,她所作的第二个解释肯定是不成立的。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终于给了她一个满意的解释。当然,这主要还是由于我对她过去的经历有很深的了解。
这个女病人从小便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很小就由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大姐抚养。在常到她家拜访的亲友中,她遇到了一位使她一见倾心的人物。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快到了谈论婚嫁的阶段。但这段美满良缘却因为她大姐无理的反对而结束。经过这段恋情的破裂,那男子就尽量避免到她姐家来,而她本人也在奥图(这让她把破碎的爱情转移到他身上的小孩子)不幸夭折后,她也伤心地离家远去,另谋独立。但是,她却始终无法忘怀那使她一度倾心的男友,但她的自尊心却令她不愿主动去找他,而她又无法将这份爱情转移给别的向她求婚的人。她的这位恋人是一位文学教授,无论他在哪儿有学术演讲,她必定是永远在场的听众,而且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偷偷看他一眼的机会。我记得在她做这个梦的前一天,她就告诉我,这位教授明天将有一个演讲,而她也必定得赶去为他捧场。也就在演讲的前一个晚上,她做了上述那个梦,而她告诉我梦见的日子也正是演讲的这一天,所以我很清楚地看出了这梦的真谛。于是,我询问她,在奥图死后是否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她立即回答道:“当然有,我记得太清楚了。教授在阔别这么久后,也突然赶回来吊丧,从而使我在奥图的小棺木旁,再度和他重逢。”这正是我早就心中有数的,于是我作了这样的解释:“假如现在另一个男孩又夭折了,那种同样的情形,必定会再度重演。
你将回去和你姐姐厮守终日,而教授也必定会来吊丧,这样你就能够再与他重逢。这梦无非是表示了你强烈盼望再见他一面的欲望——一个你始终在内心挣扎,令你不得安宁的希望,我知道你已买了今天演讲的门票,所以你的梦是一种焦躁的梦,是对那差几小时就会达到的愿望都等不及的体现。”
为了将她的愿望给以更周全的伪装,她在梦中还特意选用了最悲哀的气氛——丧事,来掩饰那与此正相反的爱情的狂热。但是,事实上,就在她的最疼爱的奥图死亡的时刻,她仍无法控制自己对这久别的情郎所具有的满腔柔情。
此外,我还分析过一个内容大致相同的梦,但分析出来的结果,竟是与前一个病人截然相反的意义。这是一个富于机智、天性乐观的中年妇女,在她作“自由联想”时,其联想之丰富迅捷也着实令我佩服。她梦中似乎看到她那十五岁的女儿,僵死地躺在“箱子”内。虽然她本人也考虑到关于“箱子”这东西,可能隐含有某种意思在内,她仍坚定地以此梦来反驳我所主张的“梦是愿望的实现”。通过一段的分析之后,她才忽然回忆起在这以前一个晚上,她曾与许多朋友提到英文“Box”这个词能够翻译成许多德文的不同意义的词,譬如Schachtel(箱子)、Loge(包厢)、Kasten(橱柜)、Ohrfeige(掌掴)等等。由梦中的别的内容看来,很可能在她心里曾把英文词“Box”与德文的盒子(Büchse)连上了关系。而且她也深知在德国的猥亵谑语中,Büchse这个词通常是指女性生殖器。这样一分析,我们或许就可大胆地用解剖学眼光来看,她的“小孩死在箱子里”实际意味着“小孩死在子宫里”,至此,她不再否认这样说倒是符合了“愿望的实现”,就像一些年轻女子,大多不愿过早怀孕而为子女操劳。她也承认当初她怀孕时,曾祈望胎儿会死于腹中。甚至在一次与她丈夫激烈的争吵后,她曾自己用力痛击自己的肚皮,希望能造成流产。因此,“孩子的死”确实算得上为一种愿望,只是过去了这许多年,生下的孩子也已十五岁了,时过境迁,所以她一时想不出这道理来。
以上所列举的两个梦(内容均为亲人的死亡)均可列于“典型的梦”之列。并且下面我要再举一个新例子,以重申我的主张:“不管梦的内容乍看是多么地不幸,其结果仍为‘愿望的实现’。”这个梦,本来也是拿来反驳我的理论的,但并不是一个病人所提供的梦,而来自于我的法学界的朋友。
他突然告诉我:“我梦见我挽着一个妇女的手,在我家门口附近散步,这时有一辆关着门的马车,停在街旁,突然闪出一个人,走到我面前,出示他的刑警身份,而要求我同他一起去警局,当时,我仅要求他给我一些时间处理完一些事务,再跟他走……”这法学家问我:“难道你能说我内心希望被警员拘捕吗?”我只得承认:“这当然不可能,但你可要想清楚他们是以什么罪名来拘拿你的。”——“我记得是杀婴罪。”——“杀婴罪?但你当然知道,只有母亲才能对初生的婴儿下手的啊!”他尴尬地回答道:“但事实上就是如此。”于是,我再问他:“你在哪种状况下做这个梦的呢?在前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不愿意再往下说了,这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假如你不说,那我只好告诉你,这梦是永远解不开的!”——“好吧!我就告诉你吧!那天晚上我并非在家睡觉。我是与一个我深爱的女人一起睡的。而且,第二天一早醒来时,我们又发生了一次关系,而后我又睡着了。也就在那时,才做了刚才我说的那个梦。”——“这个女人结婚了吗?”——“是的!”——“你并不希望她怀孕吧?”——“是的!这样会致使我们双方都身败名裂的!”——“那么你们从未做过正常的性交吧?——“我每次都留意在射精前就出来。”——“那么我是否能这样推想,那天晚上你俩都非常谨慎地做那事。然而清晨再来的那次你却没有确实做到避孕吧?”——“嗯!也许是这样!”——“所以,我还是说这梦亦是愿望的实现,从这个梦,你能够告诉自己,你并没有生下孩子或是你已经将它杀死了。我还可以很容易地道出某些相关的地方。你可能还记得,几天前我们曾经谈论过结婚的烦恼,而找到一个最荒谬的矛盾就是,性交时做什么避孕的办法都可以,然而卵子受精形成胎儿以后,不论何种形式的补救办法,都将构成刑法上的犯罪。此时我们也曾谈到,这都是从中古世纪形成的“胎儿已具备灵魂”的理论才致使今日这种谋杀罪名的成立。当然,你也知道雷诺曾有一首诗《死者的幸福》,就将杀婴和避孕讽咏成同样的罪行吧。”——“呀!多奇怪;那天早上我曾想到过雷诺这首诗呢!”——“好!那么,我要再告诉你梦中另一个附带的愿望实现。你不是说你梦见携着一位妇女的手路过你家门口吗?你心里事实上是希望能名正言顺地带她走进你家去,并不必像现在那样偷偷摸摸地在她家偷欢。实际上,这个梦的本质——愿望的实现,即使虽是以不愉快的形式来遮掩,我们还可能再找出不仅一种情况的说明。在我对焦虑心理症的病因所作的报导中,我曾谈到“中止性交”是形成神经质恐惧的原因之一。以此看来,你经过若干次这样的性交,心中已充满不愉快的影子,因而由此导致了你所做的梦,甚至还利用不愉快的心境来伪装你意愿的实现。与此同时,你所提到的“杀婴罪”也尚待讨论。何以这种只有女人才做的罪行,会出现在你身上呢?”——“我会坦白告诉你。几年前我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我和一位少女发生关系,而致使她怀孕。因为名誉关系,她默默地自己去打胎,实际上,打胎前我真的是一点不知情的。然而事后我却有段非常长的时间一直在担心,一旦东窗事发,我该如何是好?”——“我能了解你的心情,你这回忆也说明了另一理由,让你由于一次‘中断性交’没做好,从而引起这样大的忐忑不安。”
一位年轻的大夫,因为听了我上述那个梦的分析后颇表赞同,并对自己昨晚的梦,用这种分析手段作了一番讲解给我听。他说他在做梦的前一天填报了他的收入数目。此时他收入甚微,因此他就据实地填报。然而他却梦见朋友告诉他,税务委员们对他的收入申报数字表示怀疑,认为他以多报少,以此逃税,所以要罚以重金。实际上这梦不过是掩饰了他的一大意愿——期望成为收入丰厚的名医,这同时又让我回忆起在某个故事中的一位陷入爱河却不能自拔的小姐,当人家劝她决不可嫁给坏脾气的家伙,否则婚后她会挨揍时,她却坚持回答:“我却愿他会揍我!”她对婚姻的强烈意愿到令她在婚前就已经考虑到这些不幸,并且甚至还将它作为愿望呢!
要是我把这相似于“愿望的否认”或“隐忧的浮现”为内容的、乍看之下和我理论截然相反的梦,统称为“反愿望的梦”,那我在这些梦中能够归纳出两个原则。其中之一是我们日常清醒和梦境中都常常发生的,可是我们暂且把它留待以后再提。我们现在先说第一个原则,那就是他们的梦都具有祈盼“我是错了”的原因,所以病人在治疗期间发生“阻抗”时,他们均有这种内容。事实上,我已有了足够的经验,每次只须我向病人说“梦是愿望的实现”,她们便会被引发这类“反愿望之梦”。我甚至确信,现在在读我这本书的读者,或许有这种与我理论不符的梦。至此我想再次举一个我治疗病人时听到的一个梦,用来重申这原则的真谛。一个姑娘,她的亲戚和她们所请教的专家们,都反对她继续接受我的治疗,而她仍坚持要来我的诊所就医,她做了这样一个梦:她家里人不允许她再来我这儿看病,于是她提醒我说:“你曾经答应我,假如形势必要的话,你将免费治疗我。”而我回答:“我决不在意钱的问题!”用这个梦来作为“愿望的实现”的证明材料,并非一件轻易的事,但这一类的梦,通常可通过其中所含的次要问题的解决,来发掘主要问题的根源。她为何在梦中梦到我会说出那种话?其实我从未说过那种话,而一个对她深具影响力的哥哥,曾对我做过这样的批评,所以,这个梦的目的是要解释她哥哥的话是对的,然而她并不仅仅想在梦中证实她哥哥的话,她还把它作为生命的支柱,由此也成了她生病的原因。
有一个依我的理论似乎难以解释的梦——一位叫斯塔克的医生的梦和他本人所作的解释。他梦见“自己左手食指头有初期梅毒感染”。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个梦的内容,除了不合乎愿望实现的原则以外,看来也非常合理无需再作任何解释。但是,假如你肯花费精力去探讨的话,你会发觉“初期感染”这个名词极近似于拉丁文的“初恋的爱人”,然而用斯塔克本人的话来说:“这勾起了我以前情场上的失意,而且这梦完全是带有强烈感情愿望的实现。”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一下另一个“反愿望之梦”所具的原则。实际上这个动机也是十分明显的。很多人在性体验中,或多或少有由“侵犯性”、“虐待性”转变而成的相反的“被虐性”的成分。假如他们能不使肉体忍受痛苦来满足它的快感,并且能用谦逊、慈爱的牺牲态度来表现的话,我们便可称之为“理想的被虐待症”。非常明显,这类人的梦可能均是“反愿望之梦”。然而,对他们而言,这却恰恰是一种由衷的祈盼。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达成他们被虐待的趋向。这里还有个梦:一个年轻男人,早年时曾经常虐待他的哥哥(事实上他对哥哥始终有种近乎同性恋的倾向),然而成年以后,他顿悟前非,彻底改变他的态度,后来他做了以下的梦,其中包含三部分:(1)他被他哥哥欺负;(2)两个男人正在同性恋式地相互爱抚;(3)他的哥哥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将他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变卖掉了。这最后一个梦使他从痛苦中醒了过来,但是这实际上是个被虐待者愿望满足的梦。这个梦可以如此解释:“假如哥哥真如此对我不好,不顾我的利益卖掉我的财物,那么我就能够减轻我过去所做的、对不起他的种种感情上的罪恶感。”
我希望上述这些例子,能够充分证明——在没有任何更新的反对理由提出来以前——一个内容痛苦不堪忍受的梦,其实能够解析成是“愿望的实现”。(我并不认为他们已彻底解决了这问题,这之后的篇幅里,我将会再讨论到。)我们也不要认为在解析时发现到的,总“刚好”是一些令人平时不愿意想或不愿做的事,其实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就如我们平时对不愿意提起或不愿去做的事所产生的反感那样,是我们解开梦的谜底所必须克服的阻力。虽然我们提到了梦中的反感,但它并不表明梦里就没有愿望的存在,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愿道出的愿望,甚至有些对自己也不肯承认。但是,我认为我们仍可以合理地将一切梦的不愉快性质与梦的改装放在一起想,由此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结论:这些梦都是被改装过的,由于梦中的愿望通常受到严重压抑,因此愿望的实现均被改装到乍看之下无法辨认的地步。所以,我们也能够说,梦的改装其实是一种审查制度的作业。根据一切梦中不愉快的内容所分析出的结果,我拟出以下这个公式:“梦是一种(受抑制的)愿望(经过改装的)实现。”
最后我认为还需要提一下与以这种痛苦为内容的梦稍微近似的“焦虑之梦”。假如把这类梦也算在愿望实现之列,估计对一般未受过梦析训练的人而言,它更难以被接受。
可是在此我能够简单谈谈焦虑之梦。事实上,这种梦并不是梦的解析的另一对象,它仅是以梦本身来表示出一般焦虑的内容罢了。我们梦中所感受的焦虑不过是梦的内容中所明白表示的那些念头而已。假如我们想对这种梦再作解析,那就会发觉梦中所表示的焦虑就如同恐惧症所产生的焦虑一样,它仅是由某种念头的存在而导致的焦虑。例如,从窗口掉下去是可能的,所以一个人走近窗口时应该小心些。可是我们就不懂为何对这类恐惧症病人而言,靠近窗口竟会造成他们如此大的焦虑,甚至远远超过事实上所需要的小心。同样,对这种恐惧症的解释,也能够适用于焦虑之梦,这两者相同,焦虑都附着在来自另一来源的某种意念上。
因为梦中的焦虑与心理症焦虑关系密切,所以现在我谈一下后者。在一八九五年,我曾经写了一篇关于焦虑心理症的短文,提出“心理症焦虑”起源于性生活,而且多由于它的原欲由正常的对象转移时无法发泄所致。此论点的正确性,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由此我们能够得出这种结论:“焦虑之梦”的内容大多与性有关,也就是这种内容中所附的“性欲”转化而引发了“焦虑”,以后有机会我还将找若干个心理症病人的梦例来作分析,以证实此结论,而且最终当我要完成梦的理论时,我将会再次对这焦虑之梦作一番深入的思索,来指出它们也彻底符合愿望实现的理论。